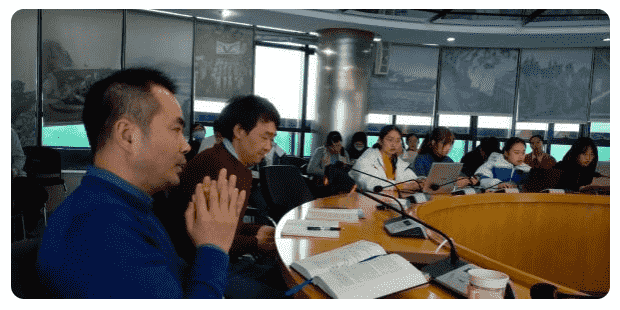
梁志(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教授):19世紀初,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大體上實現了分離。在整個19世紀,各門學科呈扇形擴展開來,彼此在認識論上的差異日益明顯,學科分化進一步加速。但值得注意的是,分與合是并行的。正如列寧在20世紀初所闡發的那樣:“從自然科學奔向社會科學的強大潮流,不僅在配第時代存在,在馬克思時代也是存在的。在二十世紀,這個潮流是同樣強大,甚至可說更加強大了。”從這個角度講,如今的跨學科研究當屬題中應有之義。在人才培養方面,2018年教育部正式提出“新文科”理念,大體包含如下含義:在堅持以人為本的前提下,對應國家和社會發展需求;實現多層次的學科交叉;在文科教育中應用新技術。落實到歷史學本科人才培養,主要呈現為培養目標中實踐導向和需求導向的強化、不同層級的跨學科教學以及虛擬現實等新技術的應用。
2020年,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思勉班”入選教育部首批基礎學科拔尖學生培養計劃2.0基地。“思勉班”旨在培養能夠將不同學科知識嫁接融合、具有復雜思維、擁有足夠的好奇心和創造力、適應信息化時代和不同職業要求的歷史學本科人才。為此,2020年11月25日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啟動了“歷史+”跨學科系列對話活動,第一期邀請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劉梁劍教授和歷史學系唐小兵教授就哲學史與思想史研究展開對話。
(一)劉梁劍教授
梁志老師從新文科的大背景出發,對我們進行“歷史+”活動作了說明。在于,在跨學科對話的過程中,會激發出我們在進入對話之前所沒有的一些想法。這是跨學科對話的魅力之所在。我最近也在思考,在新文科背景下,哲學學科應該怎樣發展?其實無論是歷史學,還是哲學,都面臨這樣一個挑戰。按照哲學系郁振華老師的學術史梳理,華東師大哲學系創始人馮契先生上承金岳霖先生,繼承了中國近代哲學傳統中清華學派的學問特點。華東師大哲學系一個重要的特點就是它比較關注哲學理論的創造,注重面向問題和對問題的分析。基于這樣的哲學傳統,我們在探究新文科背景下哲學該如何發展的過程中主要思考的問題應該是:我們怎樣才能可以更好的進行哲學的原創?在新文科的背景下,哲學原創離不開跨學科。
按我的體會,哲學史研究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哲學史家式的哲學史研究,一類是哲學家式的哲學史研究。哲學史家式的哲學史研究大概是這樣:針對某一歷史時段,把一些哲學思潮、哲學家的思想、哲學的理念等作為對象來進行把握,勾勒這一歷史時段思想演化的脈絡,獲得對這一歷史時段各個哲學家思想的客觀把握。與之不同的是哲學家式的哲學史研究,其意義與前者有所不同。哲學家式研究哲學史比較關注哲學問題,對這個問題的研究以往的哲學家推進到哪一個地步,里面有哪些還需要解決的問題,以及我們是否能做出新的推進。這樣的對哲學史的了解會比較注重以往的哲學家對問題的“洞見”,有哪些特別深刻的見解,也可能關注其中存在什么樣的盲點,即以往哲學家對問題的思考有哪些不足之處。了解洞見和盲點,最終是為了“下一轉語”,也就是在現有研究的基礎上能夠有所推進。這個“推進”,正是哲學家要探討的工作。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哲學家”對以往哲學史的態度,不是把它作為一種現成的、對象式的東西來加以把握,而是注重它該如何作為一種思想的資源,面對當下的問題來發揮作用。這大概是所謂哲學家式的哲學史研究的特點。關于哲學家與哲學史的關系,黑格爾曾經說過:哲學史是哲學的展開,哲學是對哲學史的總結。對哲學問題的探討常常要回溯到哲學史當中,因此哲學史已經變成了哲學研究的一個必不可少的工作。出于這樣一個內在的要求,不得不做一個哲學史的研究。
哲學家式的哲學史研究,關注以往的哲學史對解決當下問題的能力如何。這也就關系到另外一個問題,即“當下問題”的變化。當下問題可以是一個來源于哲學史內部的學術問題,但更加要緊更加迫切的當下問題是一個時代的問題。當我們談到“哲學是時代的精神精華”的時候,我們是在說它能夠面對這個時代所提出的問題,并給予一個理論的解決。哲學史有時直接面對當下的問題,但更多的時候它會以其他學科為中介。哲學是一個非常抽象的、形而上的學科,現實問題則是非常具體的、形而下的問題,二者之間應有一種“形而中”的聯接,這大概就是其他學科所提出的根本問題。如政治、歷史等學科對現實問題的研究已經有理論上的提煉,哲學就需要從這樣的學科里面汲取素材,作進一步的哲學思考。如果哲學在一個新的時代背景下面要真正有所推進,也需要進行跨學科的研究。我們習慣上說“文史哲”。哲學與文學、歷史具有一種天然的關聯性。例如我們這三個學科都會讀《莊子》《論語》《老子》這樣一些共同的文本,雖然彼此研究的進路有所不同。不過,另一方面,哲學又常常與科學有密切的關聯。科學技術的前沿的問題往往會推進對哲學問題的思考。在法國哲學的語境下,我們會看到,哲學與文學、藝術等的關聯特別密切,當代法國思想家會借助文學、藝術這樣的形式來對提出自己的哲學觀點。哲學要在“新文科”背景下取得發展,就需要與其他學科進行加法,并從中提取出自己真正的問題。
和哲學史研究不同的是哲學研究。哲學研究的工作特點之一便是概念分析。借助中國傳統的術語來說就是“窮理”,即對道理的“窮究”,窮究一些根本的道理。這樣的工作離不開概念考察。 “概念”與“觀念”有所不同。 “概念”與“觀念”的區別也可以延伸到“哲學史”與“思想史”研究上的區別。思想史在很大程度上會研究“觀念”,但哲學或哲學史很大程度上會研究“概念”。相對而言,“概念”的邊界較為清晰,是一種純粹邊界理性的思考。“觀念”更加趨向表達idea,我們會感覺到它的邊界不那么清晰,它不需要完全的理性,可以與感性的東西更多的關聯起來。所以如果做哲學史研究或者做哲學的考察,它會更加強調概念,在邏輯的基本框架下考察各個概念之間的關系,包括概念的歷史演變關系。而由于“觀念”與感性聯系較多,它更容易有一種推動社會變革的作用或形成與社會發生關聯的一種關系。在哲學史的考察中,對一個概念的外部影響有時不是那么的關注,反而會比較注重概念內部的那些關系;但思想史的考察會比較關注觀念及其外部條件,以及它們與社會的影響之間的關聯。
(二)唐小兵教授
關于哲學史與思想史的關系,是“相得益彰”還是“雙峰并峙”?其中隱含了一種想要使哲學史與思想史之間那些真實存在的、彼此對對方的理解、誤解等等呈現出來的意圖。剛才劉老師更多的把哲學、哲學何為、哲學史以及概念和觀念的異同等進行了一個梳理。我在這里先從一個故事講起。很多年前,那個時候華東師大哲學系主任是陳嘉映老師。陳嘉映老師比較喜歡喝酒,有一次喝酒后對一個銳意進取研究中國哲學的年輕講師說:“你研究中國哲學,可是這個前提就有疑問,中國有哲學嗎?”陳老師曾在美國讀書,接觸到的更多是西方意義上的“原初”式的哲學,是對于概念、理念等純粹形而上的研究。在他以古希臘羅格斯為原型發展出的西方哲學參照系看來,中國先秦、魏晉、宋明等歷史時期呈現和凝聚出來的經典,更多的是思想的發生史,換言之,傳統中國只有思想的歷史,并無西方意義上的哲學的歷史。在這里我們也許會追問,當“哲學”、“哲學史”等這樣的概念在清末民初進入中國,它是怎樣“落地化”、“本土化”的?中國學者又是通過怎樣的持續努力讓西方的學者認為中國有“哲學的歷史”?這是有一個漫長的爭論的。本土的一些學者嘗試用西方的學術方法來重新解釋中國的思想傳統,比如馮友蘭《中國哲學史》、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后世新儒家對中國宋明理學的闡釋,但這些著作也遭遇一種強烈的反彈與批評,認為他們都是在用西方作為一個模型和尺度來衡量中國。在我看來,這里存在一個核心問題,就是在思想史和哲學史的研究中,哲學史研究的特點是高度的形而上學和高度的概念化,而這個概念本身有它自身的生命和歷史。當我們在對一個哲學概念進行研究時,比如清華大學陳來教授關于王陽明“有無之境”的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劉述先寫中國儒家哲學三個大時代,從中你會看到他們對經典文獻中出現的一些哲學概念、觀念相互之間的異同、發展、延替做出了一些非常細膩的辨析。這個“辨析”,更加趨向于一種高度抽離歷史語境的論述,在這樣的論述中,他會認為概念本身是有其生命和尊嚴的。
這里就有一個問題想和梁劍兄討論:一方面我們會看到一個哲學概念是不會完全依賴于哪個具體的歷史情境的,是脫離context而存在的,有其內在的尊嚴和自主性;另一方面,在思想史的研究中,無論思想還是觀念,我們更多地會認為它依托于一個具體的時代語境、思想語境和個體的生命處境而形成的,如陽明哲學興起背后隱含著有儒家政治理想的讀書人得君行道的路徑被阻塞后面向民眾直接覺民行道的價值取向。因此,如果說哲學史的研究更多地是要高度的抽離、跨越,而思想史的研究更多的要還原,還原到具體的歷史語境中看他的思想觀念的衍生、凝聚和變異過程。這中間便存在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當一個概念被認為是具體的歷史情境所影響而形成時,是否會導致我們對任何時代形而上學的概念或觀念的理解走向機械的決定論?概念和觀念本身的自主性何在?一些人將思想史研究視作比較低階的學問(相對于哲學史的高度概念化操作),將其認作是從報刊雜志中的討論進行簡單地、表面化地選取和聚合,沒有呈現出觀念、概念背后深層次的意義,認為思想史并沒有一種理論結構去介入輿論話語背后的隱藏文本,因此被哲學史研究所輕視。與此同時,做思想史研究的學者也會去追問哲學史研究是否割裂了哲學家與時代之間的關系?歷史性在哲學概念的產生中到底扮演著怎樣的角色?歷史性和具體性會損害概念的自主性還是會幫助我們理解時代賦予概念的特殊意味?思想史和哲學史,究竟是“相得益彰”,還是“雙峰并峙”甚至形成相互輕忽的鄙視鏈?
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思想史和哲學史之間都存在一種區隔,哲學史中的“史”是如何展現歷史的維度的?這里舉余英時先生的例子來做一些具體的解釋。余英時先生《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一書出版后,除了在史學界,在哲學史研究界引起巨大反響。從前我們講到朱子學等宋代儒學,更多的是牟宗三等新儒家等學派那樣高度抽離歷史語境和概念化的哲學史研究。而在這部作品中,余英時先生把朱熹的思想放在宋代的政治文化背景當中,將其放到各種士大夫官僚集團的政爭中來看“以天下為己任”、“共商國是”等這些核心觀念背后的現實指涉。在那樣的政治語境中,他們試圖用這樣的方式來獲得一個得君行道的空間來實現自身的政治抱負,或者說回復到三代之治的黃金時代。這樣的還原把概念的歷史重新放回歷史語境中,從外在的視角看思想本身產生、蔓延的歷史,研究其在那個時代成為支配性主導觀念的原因。該書出版后,陳來、劉述先等儒家學者先后發表文章對此進行討論。其中,楊儒賓先生在評論文章中對余英時先生的著作提出了嚴厲地批評,他認為余先生的書從政治的、社會的、文化的語境來闡釋宋儒的基本觀念,無異于摧毀了朱熹的價值世界。對此,余先生寫《我摧毀了朱熹的價值世界嗎?——答楊儒賓先生》一文對楊的批評進行回應。文中所呈現的,正是哲學史與思想史之間那樣一個隔閡、誤解、融合、溝通與互動以及一個相互理解的可能。當特別多的學術研究只是從一個形而上學的概念來理解一個特定時代的具有共通性價值的觀念和概念時,余先生獨辟蹊徑,從一個歷史文化的角度切入,把價值觀念背后的歷史意涵和政治意圖呈現出來。
思想史研究更多的是想把外在理路和內在理路相結合,所謂外在理路就是從一個時代特定的政治文化、社會風氣、經濟狀況、內外交往等視角去看思想觀念是如何在士人回應時代關切的歷史情境中具體地形成的,上述余英時先生對于宋代一些基本觀念的研究即屬于這一理路。所謂內在理路就是思想的傳播、流傳、轉譯、接續等,有其自身的一套基本的觀念和核心的問題,這一組具有內在邏輯關聯性的問題就構成了一種延續性,如余先生對于中國思想史的明清更替,從尊德性到道問學的歷史轉型的研究突破了以往僅僅從清代政治文化和文字獄等視角的展開,而是從思想史的內在邏輯來考察。內在理路和外在理路具有互相調適、轉化的可能性,雖然思想史研究本身在歷史學研究是邊緣,但也因此而具有了一種內在生命力。歷史研究所構成的,其實是不同學科的一個“最大公約數”,如果一個學科有對自身學科形成的歷史脈絡的內在化的自我理解,歷史在其中是必不可少的。很多學科都在不斷“+歷史”,而歷史反復被“+”后,對于我們歷史學本身來說,是福是禍?歷史研究的本身完整的自主性在哪里?思想史研究本身完整的自主性又在哪里?“+歷史”是讓歷史學在不斷加厚,還是讓歷史學變成一個公共的學術工具,成為一套大家都可以用的方法?這背后意味深長。剛剛劉老師提到馮契先生,他曾經說過“不論處境如何,始終保持心靈自由思考,是愛智者的本色。”追念馮契先生與本系前輩陳旭麓先生之間的深摯的交往和學術互動,對于我們今天跨出自己所在的學科,真正獲得一種跨學科的視野和生命力特別富有啟發性。我總在想陳旭麓先生的名著《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之所以能有別于其他的歷史學著作,彌漫著一種基于歷史事實認知基礎上的“思辨”氣質,我想其中或許有他們朋友之間漫長友誼所投注的影響。馮契先生與陳旭麓先生之間的友誼,恰恰證明了各自要打破學科的壁壘,走出去用更為開放的心靈面對和吸納其他學科的滋養,形成學科之間的對話,這也更加有助于年輕學者的成長。
三、嘉賓學術對話
劉:哲學史與思想史有時還是很接近的。我們對比馮契的哲學史著作《中國近代哲學史的革命進程》和李澤厚思想史著作《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可以思考它們的研究存在怎樣的區別。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看到相近之處。比如,考察他們對嚴復的哲學史研究和思想史研究時,會發現他們相近的地方大于他們區別的地方。
唐:這是不是因為李澤厚先生是哲學家?
劉:在《中國哲學百科全書》中,其中一個條目寫中國大陸建國以后的哲學家,其中只列了兩個人,一位是馮契,一位是李澤厚,把他們的哲學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新成果。雖然李澤厚的研究叫做“中國思想史論”,但還是有很濃的哲學色彩。他在后記中談及自己的方法論時,我們發現他的思想史研究在很多地方都可以完全歸結為哲學史。我舉這個例證是想說明這兩本書對思想史和哲學史的研究很多都接近概念或觀念的考察。現在我們再來談一下哲學史與思想史的差別。考察某個思想,哲學的進路是要進入思想內部,進行一個類似概念的考察。但對于一個思想史的進路來說,它會更加注重“如何想到這個問題”,會比較注重提出那個思想時的外部狀況。因此唐老師提到的陳嘉映與學生的對話就十分重要。但這些對哲學史的考察來說是比較邊緣的,可能只需要一個發生學意義上的描述,在哲學史的書寫中甚至可以不用提及。哲學史的研究更加注重一個思想是怎樣的。在哲學課堂上討論某個思想,如果同學思考的是這個思想具有怎樣的社會的、經濟的背景,一個哲學系的老師通常是不滿意的,認為這并不是哲學思考問題的方式,因為哲學更需要討論的是思想本身。在這里我有點困惑的是剛開始提到的一個很有意思的區分,也就是內在理路和外在理路的區分。概念的內在理路較之思想史的內在理路可能更加內在,思想史的內在的理路對哲學來說可能還是一種外在的理路。歷史有不同的層面,哲學史意義上的歷史可能更多的是一個概念展開的歷史過程,這個歷史過程在具體的哲學家那里會有不同的呈現。另外,一種歷史觀之所以有這樣一個呈現,它會與哲學家本人所在的歷史語境形成一種關聯。
唐:人是具有歷史性的,哲學家頭腦中的觀念是在不同時空下概念的運動,概念相互之間的承接、運動和往返,其實還得依托于一個個具體哲學家的頭腦,而這個頭腦本身就是在一定歷史語境下成長起來的,對一些事情的思考雖然未必與其現實處境一一對應,但肯定會有一定的關系。如果我們在此只做減法,把具體的歷史語境剪掉后去考察概念本身,對于哲學史寫作或哲學史研究來說,是不是就變成一種去時空的行為?當我們在讀英國哲學家羅素的《西方哲學史》時,在其中仍然可以感受到一種很深的時空感。
劉:哲學史有不同的解法。很多人說黑格爾的哲學史更加接近哲學的概念,而羅素的《西方哲學史》更具有背景性。我們可能會認為羅素的作品可讀性比較強,但它并不是一個比較好的關于哲學研究的歷史的敘述。哲學作為一個對思想和概念的考察,去除歷史語境的同時再語境化,以獲得一種超歷史的普遍性。
唐:余英時先生的學生田浩寫過一本書叫《朱熹的思維世界》。余先生的《朱熹的歷史世界》更多的是從歷史學的角度敘述,而田浩的書更多的是一個思想史的研究。我也曾把田浩的書與其他學者的書進行比較,我們會看到:如果說思想史的研究會把思想者觀念的提出放到個體生命的成長過程和與同時代學者的交往結構當中,我其實也不太贊同把最一流的學者或哲學家的思想觀念歸于一種庸俗的決定論;另外我也不贊成一種高度的概念化的敘述,因為目前時髦的概念史研究很大程度上抽離了歷史語境,所以概念史在歷史學領域流行的同時也備受批評。
哲學家式哲學史研究的一個意涵,講究“洞見”,歷史學也同樣如此。一份好的研究不是通過很多研究的個案而得出一個前人已有的研究結論,為前人的論證做腳注,即只能為前人的結論豐富史料論證,而不能有所創見,沒有穿透、提升和拓展。“洞見”對歷史學來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洞見”從哪里來呢?這是我們每位同學都要思考的問題。史料在那里,只要夠勤奮,能夠利用新的技術去搜索,多少都會找到。而作為敏感和洞見的史識來自何處?是我們應該思考的問題。史識本身特別重要的來源,就是“跨學科”,而不能只是學術的內卷化,只在史學內部進行觀察。走出學科之外,形成新的研究視角,提出在歷史學內部自我循環時看不到的問題。但中國學術界的跨學科有一個問題,我們的跨學科表現得太過簡單,似乎搬用幾個其他學科的概念或名詞就完成了跨學科,這僅僅是一種徒有其表的象征性跨學科,甚至是為跨而跨的跨學科,真正的跨學科應該是我們真正了解人類學、社會學、政治學等學科他們的基礎問題和核心課程內容,獲得一個真正的跨學科思維,而不只是一個新名詞的炫耀性使用,真正尋找到跨越和提升的動力。我們思勉班的同學應該始終保有開放的心靈和態度,走出去又回過來,讓“歷史+”對話成為一個契機,不斷拓寬自己的學術格局,提升自己的學術境界。
劉:在歷史學的研究中,“洞見”不只是一種材料的堆砌。與此同時,這種 “洞見”也同樣認為生活世界是非常重要的。在生活世界中,一個好的史家應該是有一種關切的,對國家、對世界文明的一種關切,成為史識的根本來源。從王家范先生等人身上,我們都可以看到這種精神,這樣的精神比“洞見”更加重要,是一種作為學術底色的存在。
唐:一個學者、學人的精神底色是非常重要的。我們的同學在華東師大這個人文空間和學術傳統里面成長,要努力進入到這個人文的傳統和脈絡之中,形成精神的品格與底色來面對學業、生活和挑戰。歷史學不僅提供了一個思考的契機和資源,它同時也讓我們進入到那些歷史學家的生命世界,看到他們是如何面對他們所處時代的一些波折的。我們同學都會面臨各種現實的學業和方方面面的困擾,而這些傳統會給我們提供一些安身立命的基礎,不但有知識的意義,還有精神的價值。
四、嘉賓與學生對話
學生提問:我們今天講哲學史和思想史的差異較多,那他們之間又具體有什么樣的相似之處呢?我們又該以何者為切入點來促進二者的融合呢?
唐:我們在這里更多地談哲學史與思想史二者之間的差異,更多的是希望展現出一種“相得益彰”“和而不同”。他們之間的“同”可能更多地體現在都注重對思想觀念的闡發、理解和辨析,這與哲學研究中概念的透視具有一定的相通之處。所以無論是做思想史還是做哲學史,對人的天分要求都非常高,要求研究者具有一種縝密、有邏輯感的思想能力。現在很多的思想史研究太過于簡單化,而思想本身是具有內在的生命力的,其內部的縝密結構在思想史研究中并沒有得到很好的呈現。因此,我們要讓思想史給哲學史增加一點歷史的底色,讓哲學史給思想史增加一點概念式的抽象思維,實現二者之間的共同促進。
劉:我們回到上面所列舉的哲學史與思想史的例子。馮契先生研究中國近代哲學史更多是一個哲學史的研究,他把從中國古代開始就形成的一個比較重要的哲學問題的內部框架,用這個框架來理解近代的思想家和哲學家對這個框架的貢獻。后來,馮契先生的學生高瑞泉老師在研究中國思想史的過程中,形成了這樣一個研究體會:他慢慢覺得馮契先生的哲學研究方法對于中國近代思想史來說意猶未盡。這與中國近代哲學自身的特點相關。中國近代的思想家中很少有人提出了非常系統的哲學思想,所以對他們的研究可能更多地都指向一種觀念。由此,我們對中國近代思想的研究,有必要從哲學史走向思想史,突破哲學的線路,做一個跨學科的研究。
來源:澎湃新聞